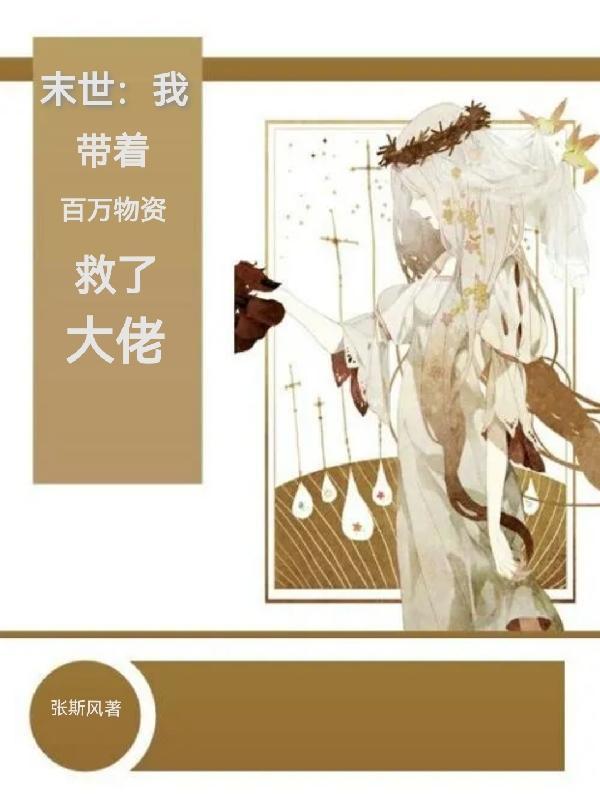91言情>徐总又咋了 > 第44章(第2页)
第44章(第2页)
梁璋歪在座椅上,默默把空调出风口拨弄向驾驶座那边。
高速路上车辆稀少,只偶尔掠过一些反光的道路标识。近光灯里无数飘洒的雪片朝他们袭来,夜色深沉,他们正在逐渐驶离北京。
换梁璋开车的时候,徐培因直接把副驾摊平了,裹紧大衣睡过去。明明说自己白天起得晚,结果还是很能睡。
过土路的时候把徐总颠醒了,迷迷瞪瞪爬起来,项链坠在衣领外随着颠簸乱晃。他扒着车窗看外面简直荒郊野岭,但也近人烟了,周围有爆竹烟花响起,天不再是浓黑。“要不是有爆竹声,我以为你给我卖了……”梁璋瞟一眼后视镜,徐培因幽幽盯着他。
他笑了:“马上到了,这儿是我二表姑家,她家全家出去过年了,没人在,我们去她院子放炮。”
他把车停在门口,开始按照二表姑的微信指示翻哪块砖头底下藏着大门钥匙。雪把砖块都盖上了,并排的每家都在放炮,窜天猴的声音一会儿一个,梁璋哈着白气蹲在哪里刨雪,让培因哥先下车等他。
“冷吗?”梁璋扭过头大声喊培因哥,“冷的话你跺跺脚!”
徐培因跑过来踹了他一脚,梁璋又笑。
南头谁家点了个二踢脚,梁璋从仓库里抱出烟花箱的时候,看徐培因本来正低头用鞋尖在雪地里画着什么,被突然的巨响吓得缩脖子,好半天才从羊绒围巾里挣出半张脸。
不经吓的人还能点炮吗?梁璋保持怀疑,但还是往地上铺了一长串挂鞭。
“带火了吗?”他问徐培因。
徐培因从兜里摸出个打火机给他,原先都是梁璋点烟,他才见到培因哥的打火机,是只银色的登喜路。
“……”梁璋把打火机又放回他兜里了,去里屋抽屉找出盒火柴,放他手里,“你点吗?拿这个点吧。”
徐培因划了支火柴,背对他躬着身子去点引线。挂鞭的引线长,留了充足的时间,但梁璋就爱吓唬人,火更着起来就大喊:“快跑!”
培因哥很听他话的转身,踩着碎雪往他这边小跑过来,没系上扣子的大衣摆让北风灌成帆了。梁璋下意识张开双臂,结果徐培因急刹在两步开外,只铲到他身上一点雪沫。
“干嘛,”徐培因微微喘,指着他笑,“我不抱……”他的尾音被后面鞭炮的炸声吞没,梁璋趁机抓住他指向自己的手,把人结结实实拽进怀里。
“你说什么,我没听清!”梁璋抱着人,贴到他耳畔装傻,“新年好啊,徐培因,今年要顺风顺水顺财神!”
那挂鞭炮有一千响,徐培因不可能让他抱到鞭炮声结束。
“我梗系希望你好啦,冇病冇痛,冇灾冇难,做乜事都顺顺利利……”培因哥摸摸他脑袋,“你开心嘅话,我梗系都开心啦”
一长串下来天书似的,鞭炮又吵,梁璋摇头:“哥,听不懂,要普通话。”
徐培因大声说:“身体健康,今年好好给我干活!”
“当然啊!”
他们又点了许多烟花,爆到天上一片片,要仰头看。
梁璋侧过头看徐培因,他围巾散开了一角,鼻尖冻得通红,眼里不断映出红黄的烟花,脸上又让满地的雪色打了光。
“别老盯着我。”培因哥撞他肩膀一下,梁璋只好也仰头望着天。
徐培因也不是神啊。梁璋给他叠了桃色的、纯白的滤镜,哪里都好,每寸皮肤肢体看到都起欲勾瘾。用不带情欲的眼光看这么漂亮的脸对他来说是很难的事,最近才发现自己可以做到。于是发现培因哥其实挺坏的,拒绝他还做朋友什么的,简直是吊着他,太坏了。
培因哥并非白璧无瑕,他却越来越喜欢他。
烟花箱空了大半,徐培因在院子里扫地,梁璋去屋里整理床铺,两个人要睡一觉才能回北京。
表姑家孩子不回来的时候孩子那屋都锁着,好在双人床很宽广,两个大男人也不算挤。
外面爆竹声稀了,梁璋听见徐培因在枕边叹气:“烦死了,忘带眼镜过来了。”
“没事,我当你盲杖嘛。”
“我没真瞎!”
梁璋笑两声,手伸到对方被窝里,去戳他的腰。然而徐培因居然没有痒痒肉,反过来把梁璋摸得狂笑不止。
“不行,不行了……”梁璋上不来气了,举双手投降,“我错了,别玩我了。”
徐培因坐在他身上,拍拍他的脸:“非要这样才老实。”
“好嘛,睡了睡了……”梁璋说着,培因哥却低下头,在被子下轻轻吻他。
被窝都串了,培因哥问他:“要不要做?”
梁璋心跳如雷,想着徐培因坏到家了,他是没有那么冲动了,但又不是和尚。“这是我二表姑家!”
“哦。”
徐培因从他身上下来,梁璋又重新把他塞回自己的被窝,被角都掖好。
培因哥说:“想回我家了。”
梁璋躺好,转过去隔着被子抱住他。“睡醒了就回去。”他轻轻拍着徐培因的后背,“很快回家的。”
……
天亮后徐培因没戴眼镜,摸着桌子走路让梁璋笑了好久,气得不讲话了,回去的路上梁璋只好一个人安静着开了四个小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