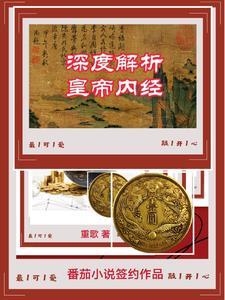91言情>不是,你没病吧你爸爸单奇鹤一会儿 > 第121章(第1页)
第121章(第1页)
“你听说过人格分裂吗?”
“我是副人格。”
……
薛非身体又往后退去,直到差点从床沿边掉下,跟单奇鹤表白的时候,他说自己可能会消失。
薛非艰难地开口:“……你不是他?”
那双眼睛又缓慢地闭上,睫毛震颤,他不说话。
薛非掀开被子坐到了地板上,他愣神了许久,直到床上躺着的那个人发出了些难受的哼声。
薛非站起来,把被自己弄乱的被子重新整好,让热气留在被子里:“你要喝水吗?”他很冷静。
单奇鹤没有说话。
薛非给他换了退烧贴,又喂了一颗药,外面的天亮了,躺在床上的人还一直没有睁眼睛。
早上十点左右的时候,单奇鹤又烧了起来,浑身滚烫。
薛非面无表情地把人从被子里挖出来:“去医院打针。”
他把衣服给单奇鹤穿上,裹着严严实实地,把浑身没力的人背到身上,出门的时候,他脸上的肌肉几乎不可控地颤抖起来。
他仰头呼吸。
背着单奇鹤走了好几个附近私人诊所——过年了,都关门了。
中午十二点好不容易找到个开门的诊所,他把单奇鹤放下。
医生以为人是昏迷的,皱着眉头准备让赶紧送到市医院去,病人睁开眼睛看了一眼医生,医生吓了一跳:“醒着的啊?哪里不舒服,发烧多久了?”
单奇鹤不说话,薛非站在他身后,明明表情平静,却总莫名让人感觉像是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,薛非语气僵硬:“昨天下午烧的,最高烧到了三十九度七,后半夜降下来了,今天早上又烧了,吃过两次退烧药。”
医生哦了两声,开始给单奇鹤看病,后来给单奇鹤挂吊针,单奇鹤又闭上眼睛似乎睡着了。
薛非走出诊所,茫然地直接坐在了马路牙上,他仰头看天,又低头看地面,两片叶子藏在透明的塑料袋下,风一起来,塑料袋飘到了天上,薛非垂下头,而后背脊越来越弯,最后整个脑袋都埋到了膝盖里,连风都安静了。
他不知道该想什么,又觉得这种愚蠢的、骗人的玩笑,当然不该当真。
单奇鹤在生病,神态、眼神和健康时不一样,应该很正常。
薛非无数次告诉自己,逐渐坚定想法。
可下一秒却有想法,如同一根针似地不被期待地扎入他大脑。
——如果真的不是一个人,那怎么办?
我怎么办啊?
-
单奇鹤的吊针挂了将近三个小时,薛非又把人背回了家,他全程一言不发,脱掉了单奇鹤的衣服,把人塞到被子里。
他伸手搓了把脸,趴在床边休息,他什么都没想,脑子空空,只希望单奇鹤的病赶紧好起来。
拜托拜托。
第二天单奇鹤退烧了,薛非在床边地板上坐了一夜,手机里塞满了很多条消息和电话,他把前一天熬的粥吃了,问躺在床上睡着的单奇鹤:“你要吃点么,不吃东西好不起来。”
床上的人在睡觉,没有开口说过话。
薛非面无表情地喝完了一碗粥。
晚上的时候,外面开始有爆竹和烟花的声音,薛非把窗户打开一条缝,站在窗户边。
他把单奇鹤的烟拿出来,迎着窗户和来冷风给自己点了根烟,耳边似乎能听见风带来哪家那户的欢声笑语。
薛非垂下眼睛,吸了口烟,尼古丁穿过喉咙进入肺腑,他压下了一点咳嗽声,没什么情绪地望着屋外,屋外有些地方挂了灯笼,透露出些喜气洋洋的气息。
他屋内灯都没开。
大年三十了。
再过几个小时都到新年了。薛非的手指拨了几下,单奇鹤买的摄像机,几天没充电,这东西没电关机了,他也懒得充电,没意思,干什么都没意思。
等到屋外的灯暗了,周围吵闹的笑声也变小了,薛非抽完了单奇鹤带来的一整包烟,他走到盥洗室洗了把脸,走到床边坐在地板上。
他盯着单奇鹤睡着的脸看,烧退下来后,脸不那么红了,之前喂了两杯水,嘴唇也不干了,此刻呼吸平缓,好像只是在睡觉。
薛非本来在地板上坐得笔直,而后忍不住凑过去,他用手指隔着空气,描绘着单奇鹤的五官。
他低声说:“醒来啊。”
他胳膊搭到床沿边,脑袋枕上去,通过灰暗的光线,盯着单奇鹤熟睡的轮廓。
“你舍得留我一个人过年吗?”
“马上新年了,单奇鹤。”
“单奇鹤……”
被子里的人睁开眼睛,薛非怔怔地看着,像是盯着人看,又像是在放空。
单奇鹤咳嗽了声,薛非猛地抬头。
单奇鹤的鼻子嗅了嗅,嘶哑的声音问:“什么时候了?”